作者:周舟,Foresight New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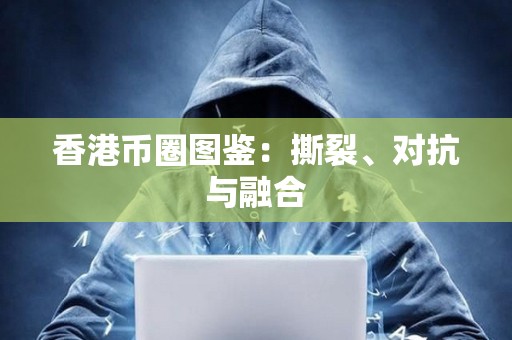
2025 年,香港幣圈的撕裂感愈發明顯。
「每天都有傳統金融機構找過來,和我們討論 Crypto 業務,我們自己也在嘗試將新業務推廣到 Youtube、X 等平臺上,找有影響力的 KOL 和博主進行合作。」一位券商從業者談起加密業務拓展時,語氣里滿是干勁與期待。
而另一邊,一名剛入職不久又選擇離開的區塊鏈公司員工卻語氣低落:「我走了,受不了這種國企作風。」
同一個香港,同一個加密貨幣生態,有人感受到的是行業經濟上行帶來的興奮與機會;也有人感受到的是體制與文化摩擦帶來的倦怠與失落。戲劇性的撕裂,每一天都在上演。
一方面,幾乎所有主流香港券商都已經涉足加密貨幣業務。最新統計顯示,香港已有超過 40 家券商、超過 35 家基金公司、超過 10 家大型銀行與大型會計事務所涉足虛擬資產業務。比如香港最大的科技券商富途牛牛早在去年 8 月已經為客戶提供比特幣和以太坊等虛擬資產交易服務,到去年年底,其日均交易量已經超過 3500 萬美元。
從券商、基金、銀行、審計再到保險,香港主流金融機構正在有條不紊的、全面的將加密貨幣納入香港的金融體系中。這讓部分跨界涉足加密貨幣行業的金融從業者們感覺到了久違的創新氛圍和一種「行業經濟上行的美」。
然而,在另一方面,部分加入到合規公司的 Crypto Native (加密貨幣原住民們)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幻滅——曾經堅信的去中心化烏托邦,正在與現實的監管、合規和金融邏輯不斷碰撞。既想要保持 Crypto Native 的「風格」和「調性」 ,又想要在合規行業分一杯羹,這正在成為他們難以化解的矛盾。
香港加密貨幣行業,正在三種主要文化的不斷撕裂與融合中,逐漸孕育出一種新的物種。
第一種文化是 Crypto Native。
比如 HashKey 與 OSL 等早期的香港合規加密貨幣交易所,吸納了不少從 Huobi、Bybit、Binance 等公司跳槽而來的 Crypto Native 從業者,這使得這些公司的文化底色仍然相對「原生」,保持著開放、靈活、市場優先的氛圍。
和 Digital Native (數字原住民)類似, Crypto Native (加密貨幣原住民)深諳鏈上世界,天然具有對加密文化的敏感力與創造力,相信去中心化與技術無國界。不過目前來看, Crypto Native 的從業者似乎正在不斷被稀釋,更多互聯網金融與傳統金融的從業者進入到這一行業,并迅速在合規框架下占據主導。
第二種是互聯網金融文化。
富途、螞蟻集團、螞蟻數科、京東等,都是典型代表。它們帶著成熟的線上運營和用戶增長經驗,正在積極切入香港的加密貨幣市場。其中,有的已經較好地融入香港的主流金融文化。以富途牛牛為例,作為香港最大的互聯網券商,它不僅在線上牢牢占據市場,還在香港最繁華的街區開設了 6 家線下實體門店,展現出強烈的互聯網金融基因與本地化結合。
在香港線下實體店走訪的過程中,一位富途的線下員工熱情的幫筆者開通美股賬戶,并向筆者表示:她每周大約會接待一百多名前來咨詢美股、港股、加密貨幣等服務的顧客。「目前香港戶口可以辦理加密貨幣業務,但是內地身份證的用戶不可以。」該員工表示。
據悉,富途控股注冊用戶數已超過 2625 萬,其中富途牛牛牛在香港成年人口的滲透率已經超過了 50%。海量的存量用戶,讓其在香港加密貨幣市場上有著天然的優勢。一位業內人士透露,富途香港用戶的加密貨幣交易目前依托 HashKey Exchange 的底層交易系統進行,該部分交易量已經占據 HashKey Exchange 整體交易量的相當大比例。
富途之外,螞蟻和京東也在角逐「香港加密圈」。不過和富途專注在加密貨幣交易所領域不同,螞蟻和京東更專注在穩定幣和公鏈賽道。富途已經有牌照傍身,而螞蟻與京東是否拿到牌照依然是一個未知數。
香港加密貨幣行業不是一個完全市場化競爭的賽道,而更像是一個拼資源的地方,需要拿到牌照才能上桌。一位業內人士透露:中資銀行拿到首批穩定幣牌照的可能性更大。
第三種文化是香港傳統金融文化。比如匯豐、中銀香港、勝利證券等。他們是在香港金融業有著更悠久歷史的文化,其中有的是外資背景在香港,有的是中資背景在香港,有的是香港本土家族背景。他們也將形形色色的文化加入到了香港加密貨幣行業中。
如今,香港的加密貨幣行業已經發展出一條覆蓋上百家金融機構的合法產業鏈——從券商、基金、銀行、審計,到保險公司,每一環都在合規框架下運作。
從地域和背景來看,這條產業鏈涵蓋了外資、中資以及本土機構;從技術與制度角度來看,則匯聚了 Crypto Native、互聯網金融企業以及傳統金融機構。他們共同構成香港加密貨幣行業的多元生態,支撐起本地加密資產市場的穩健發展。
不同的文化之間的撕裂與融合,在塑造這一新的行業。
香港幣圈,不再是一個可以簡單被定義的存在,它已經是一個涵蓋了 100 多家香港金融機構的獨特的復雜系統。
同一個香港,同一個生態,但是每個人對香港幣圈的感受卻截然不同。
有從業者覺得合規化的香港幣圈,正在釋放一種經濟上行的美。
比如在某些剛跨界涉足加密行業的傳統金融從業者,比如已經或者正在申請交易所或者穩定幣牌照的公司,比如本身便手握大量用戶只需拿到牌照便能開拓市場的互聯網金融巨頭們......他們表現出了一種強勢的勁頭。
這在招人上表現的異常明顯,比如富途、京東、勝利證券等公司,他們在市場上表現出了對人才的強烈渴望,正在以比市場價更高的價格挖人。
但也有從業者覺得香港幣圈,已經進入階段性的存量市場,進入到了下行周期。香港的加密龍頭企業沒有找到做大蛋糕的好的方法,只能無奈進入搶蛋糕的惡性循環中。
「對,我走了,受不了這種國企作風。」一名剛加入不久便離開的某大型機構背景的公鏈的員工表示。
「少了很多主觀能動性,做什么都要先看監管。」面對從原生加密貨幣行業到合規加密貨幣行業后工作內容上有什么明顯變化的問題,一位加密合規交易所中高層管理者回答到。
還有一些從業者的撕裂感的來源在于 Crypto Native 與合規圈之間在文化與制度上的巨大差異。
最近一次引發不少 Crypto Native 「不滿」的事件是 2025 年 8 月 1 日正式生效的香港穩定幣法案。「我從沒見過哪個穩定幣,是需要 KYC 的,也從來沒見過哪個穩定幣,是需要限制 VPN 的,這還怎么創新發展?」一名從業者抱怨道。
對于浸泡在 Crypto 和區塊鏈文化里成長的從業者們而言,他們習慣了一切由代碼和社區驅動的生活,而如今香港合規加密貨幣行業一切由政策驅動,這從本質上形成了兩種生態。但是許多從業者仍沒有做好在不同生態切換視角和立場的準備。
香港特色的加密貨幣行業,正在經歷一場由政策主導的強行融合后的陣痛。這種陣痛不僅關乎政策與制度的磨合,更深層地觸及到傳統金融文化、互聯網金融文化與加密原生文化之間的沖突與調和。
一個新系統的誕生之初,往往會出現一些讓早期參與者們「悶聲發大財」的機會。他們在跨界中分到了第一杯羹。
比如穩定幣誕生之初,Tether 曾在一年之內讓交易量增長了 100 倍,2017 年年交易量超過了 1 百億美元,2020 年年交易量超過了 1 萬億美元,而 2024 年則超過了 10 萬億美元。再比如幣安誕生之初,前兩個月的日交易量超過 1 億美元,第四個月日交易量便超過 10 億美元,第六個月日交易量超過了 50 億美元。
當然,香港目前并沒有出現業務如此快速增長的公司,但這并不意味著沒有公司在這個過程中吃下了第一波紅利。
「最近每天都有傳統金融機構找過來,想和我們討論 Crypto 業務,我們自己也在嘗試將新業務推廣到 Youtube、X 等平臺上,并且找有影響力的 KOL 和博主進行合作。」一位正在涉足加密貨幣業務的某香港券商從業者表示。
「隨著香港擁抱加密貨幣,上百家 Web3 公司入駐香港,咨詢政策、申請各類牌照、開拓各類業務都需要咨詢律所,這給部分專注于加密貨幣合規方向的律所提供了大量的業務需求。」一位對律所熟悉的加密從業者表示。
「每個想要在香港長期發展的 Web3 公司,都會申請一個香港公司銀行賬戶,在此產生許多流水,這也給了那些早期看重這一塊業務的銀行,比如眾安銀行等帶來不少業務。」一名香港合規交易所的從業者認為。
香港加密貨幣行業的機會,可能并不只在于人們傳統印象中的交易所、資管和穩定幣公司,那些在香港加密行業發展中提供「賣水人」服務的機構往往也是受益的重要一環。
而那些真正在悶聲發大財的公司,也往往在數年之后,才被公眾知曉。
「對 Crypto Native 來說,香港的合規加密公司創新速度太慢了,還帶著點官僚甚至國企的氣息;而對香港的傳統金融機構而言,今年的創新 KPI 可能早就超標了。」一位加密合規交易所的中高層管理者這樣評價。
在不同的視角下,香港加密貨幣行業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樣貌。
對于浸泡在 Crypto 與區塊鏈文化中成長起來的從業者,他們習慣了一切由代碼和社區驅動的節奏。然而如今的香港加密行業,卻是一切由政策驅動。這里不再有草莽的氣息,創新的鋒芒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合規的穩健與克制。許多 Crypto Native 感受到:香港的合規正在「閹割」幣圈的原始創造力,這種排異反應讓他們無所適從。
而對于部分在傳統金融行業習慣了安全和穩定節奏的從業者們而言,香港 Crypto 的創新節奏并不慢,而且正在有條不紊的發展中。慢,才是快;快,才是慢。
而身處在這一時代洪流的從業者們只能適應。無論熱愛還是抗拒,歷史的洪流終將滾滾向前。
<strike id="ykeqq"></strike>
<fieldset id="ykeqq"></fieldset>